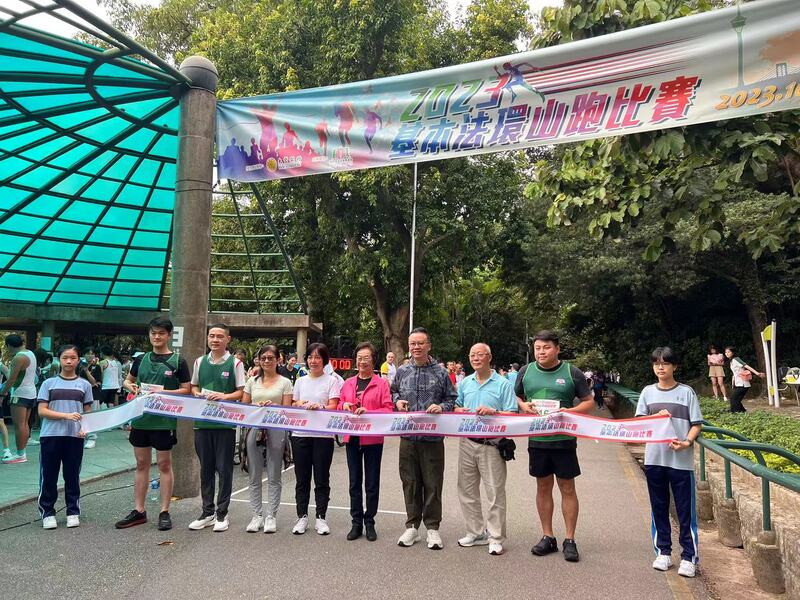一、中央的全面管治权
(一)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具有全面管治权
(二)中央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治理结构中的角色
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一)高度自治权的性质
(二)高度自治权的内容
(三)高度自治权的法理逻辑
三、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运作模式
(一)两个权力运作的政治前提
(二)两个权力运作的宪制基础
(三)两个权力运作的相互衔接
四、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途径
(一)全面管治权引领高度自治权的有效行使
(二)全面管治权支持高度自治权的依法行使
(三)全面管治权监督高度自治权的正确行使
五、小结
一、中央的全面管治权
(一)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具有全面管治权
“全面管治权”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对所有地方的所有事务进行管辖和治理的权力。中央对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是指我国基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而产生的对特别行政区进行管辖和治理的权力。其内涵包括:
第一,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对澳门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载体。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同的特别行政区域划存在,如秦汉的属国和道,南朝时期的左郡左县制度,唐宋的羁嬷制度,明清的土司制度。[1]这种特别行政区划制度是整个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里的一种例外和补充。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我国在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采用不同于内地的管治制度和管治方式,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这种特殊管治制度和管治方式本身就是在整个国家管理制度下运作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对澳门恢复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载体。
第二,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和授权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我国宪法在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主要有三种关系:一种是中央和省、直辖市的关系,一种是中央和民族自治区的关系,一种是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无论是普通的省和直辖市,还是民族自治区,还是特别行政区,其权力都是中央授予的,中央对这些地方都具有全面管治权。然而,中央对这些地方授予的权力内容和权力范围是不同的。其中授给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内容最广,程度最高,不仅超过了省和直辖市的权力,也超过民族自治区的权力,甚至也超越了联邦制下属邦的一般性权力,所以称为“高度自治”。中央授权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和中央保留自身行使的权力,构成了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
第三,中央的全面管治权,还包括中央对高度自治权进行监督的权力。授权是指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2]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有监督权,这是授权理论本身决定的。中央有权对高度自治权的运作进行监督,两部基本法本身就有多处规定和深刻体现。澳门基本法是全国人大根据我国宪法制定的,全国人大本身就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就有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以及解释法律的职责。[3]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监督基本法在宪法架构下正确实施的职责和职权。澳门基本法都明确规定行政长官负责执行基本法,并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就包含着行政长官就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的落实和执行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二)中央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治理结构中的角色
1主权的代表者
主权是国家的最重要属性,是国家所固有的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法国博丹最早提出了主权概念,“主权是凌驾于公民和臣民之上的共同体(commonwealth)所有的最高和绝对的权力。”[4]主权是国家得以构成的根本要素,也是国家行使一切权力的源泉,它既不可分割,也不可转让。主权既包括国家独立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也包括对其管辖范围内所行使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权力。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样就形成了澳门问题。所谓澳门问题的解决,就是指我国政府收回澳门,结束葡萄牙非法占领,并由我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中央不仅是主权的代表者,而且还是主权最重要的维护者。国防和外交是两种典型的主权权力,是维护主权尊严的重要途径。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防务和外交事务。我国政府在澳门恢复行使的主权不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权力,不只是一种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绝对的和最高的权力。这就需要一系列具体职权来维护主权的绝对和最高的属性。
2权力的授出者
在单一制国家,所有权力在理论上都是属于中央的[5],地方的权力是由中央授予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力在本质上是我国单一制下的地方自治权力,是中央通过基本法授予的。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治理结构里,中央不仅是主权的代表者和重要的维护者,而且还是高度自治权力的授出者。[6]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是授权关系,是一种授权者与被授权者的关系。
中央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授权的形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澳门基本法第2条的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赋予其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第二种形式就是澳门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还可以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从一国两制的实践来看,第二种形式的授权主要有:(1)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特区政府指定其有关机构根据国籍法和有关规定对国籍申请事宜作出处理;(2)1999年2月18日国务院授权澳门特区政府自1999年12月20日起接收和负责核对原澳门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并自主管理;(3)2009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自启用之起按照澳门法律实施管辖。
3自治的监督者
澳门回归后,其高度自治无论有多高,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特别行政区,已经成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所以,高度自治出了问题,最终是中央人民政府“买单”,特别行政区本身无法承担最后责任,“兜底责任最终在国家和中央政府。”[7]这在法律上就表现为,中央作为特别行政区高自治权力的授予者,自然有权监督被授出的高度自治权力的行使情况。在单一制国家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监督大致有以下几种方法:法律监督、财政监督、人事任免、司法监督与发出指令、视察地方等等。这些监督与控制的机制由于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的缘故,其表现出来的形式又有所不同。[8]
有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澳门基本法,中央人民政府并不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也不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管部门,而只是直辖与被直辖的关系。[9]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地方各级行政机关,这里当然也包括了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内。因此,这是一种直辖与被直辖、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不过,具体的领导方式不同于中央人民政府对内地普通地方政府而已。研究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特区政府的原则、方法和措施等问题,已经是摆在有关实务部门的现实理论课题。
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
(一) 高度自治权的性质
地方自治是指地方有权自主处理自己的本地事务,其内涵不仅是指地方处理本地事务有一定自由裁量空间,而且还指地方能够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自治机关”,形成自己的自治意思,实行自我管治。既然是自我管治,其他主体就不能随意干预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自我管治主体有权决定在法定范围内自我管治的具体方法和具体措施。[10]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有权成立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自己的行政领导人,享有较充分的决定和管理地方性事务的权力,这就属于地方自治的范畴,只是“我们习惯上没有这样去称呼它,按照我们的理论,统称为民主集中制。”[11]因此,我国是否存在着普通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应当从实质上考察,而非形式上考察,更不能拘泥于是否出现“自治”两字。[12]因此,我国的地方自治包括以下三种:(1)一般地方的地方自治;(2)民族区域自治;(3)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其自治的程度是一种依次递增的关系。因此,澳门基本法所规定的高度自治,是从比较意义上而言的,是指我国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自治,其程度不仅比一般地方的自治要高,而且也远远超过我国在民族自治地区实行的自治,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联邦制成员国的权力。澳门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实行“澳人治澳”,而且还规定实行财政自主,在经济上保证了高度自治实行的可能性。[13]
(二) 高度自治权的内容
1 行政管理权
行政管理通常是指政府对经济、文化、市政、治安、福利等方面的社会事务以及对其自身进行日常管理的行为,是政府的基本职能。[14]然而,澳门自回归后,成为我国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下的特别行政区,是我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其许可权本身就来自中央的授予。两部基本法所说的“自行处理行政事务”,只能是局限于特别行政区的地方行政事务,国防、外交和其他不属于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特别行政区无权处理。那么,在高度自治的情况下,特别行政区能够自行处理的行政事务包括哪些呢?两部基本法没有采用列举的方法详细开列特别行政区享有哪些方面的行政事务管理权。1988年《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曾经就对这些行政事务作出明确列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自行处理财政、金融、经济、工商业、贸易、税务、邮政、民邮、海事、交通运输、渔业、农业、人事、民政、劳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文化康乐、市政建设、城市规划、房屋、房地产、治安、出入境、天文气象、通讯、科技、体育和其他方面的行政事务。”[15]该草案列举了29项自行处理的行政事务,然而,行政事务不易精确分类,且容易列举不全,因此,1989年的香港基本法(草案)删去了列举的各项事务,改为现在的概括式表述。[16]这就是说,凡属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行政事务,均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管理和处理,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根据香港和澳门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实际需要,全权处理特别行政区内部的行政事务。
2 立法权
立法权通常是指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权力。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是其高度自治权的重要体现。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地方,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享有和行使立法权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称为“法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制定地方性法规,不能称为“法律”。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第18条指出,全国性法律除列于附件三者外,不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列于附件三的法律应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不属于自治范围内的法律。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除了国防、外交和其他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外,有权就其高度自治范围内的所有事务进行立法,既可制定单行性的法律,也可以制定法典性的法律。这就体现了这种立法权的广泛。
3 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澳门基本法第19条都规定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里的“独立”,其含义不仅包括独立于特别行政区内的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而且还更要的是,还包含着相对独立于内地的司法体制。终审权本是司法权力其中一种,“和”并不是指终审权与司法权并列的独立权力,而是指“及其”的意思,是指基本法把包括终审权在内的司法权一并授权给特别行政区行使。[17]
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包括以下几个内涵:(1)特别行政区法院根据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审理案件。(2)特别行政区法院法院,在依法行使司法权和终审权时,不受任何干涉,既不受特别行政区内部的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也不受我国内地司法部门和其他有关机构的干涉。(3)特别行政区司法体制自成体系,建立自己终审法院。终审法院的判决和裁决为最后的判决和裁定,当事人不能就终审法院的判决向设在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4)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18]
4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
澳门回归中国后,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澳门的外交事务,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处理。但是,考虑到澳门是国际性城市,在许多国际组织、国际条约的成员,因此基本法在规定外交权力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同时,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的对外事务。澳门基本法主要在其第七章规定了特别行政区享有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这些权力主要包括:(1)在外交事务由中央负责管理的前提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代表,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由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同澳门特别行政区直接有关的外交谈判。[19](2)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信、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适当领域,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20](3)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的前提下,在外国只能设立官方或者半官方的经济和贸易机构;[21]在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前提下,接受外国在特别行政区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立必须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批准。[22](5)在中央人民政府授权下,给持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中国公民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即特区护照,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签发其他旅行证件。(6)在中央人民政府协助或授权下,同有关国家和地区谈判和签订互免签证协议。
(三) 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法理逻辑
澳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法理逻辑,包括高度自治的权力来源和运作原则。
第一,高度自治是一种来自中央授权的地方自治。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非澳门本身所固有,而是来源于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授权。中央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全面管治权,这种全面管治权的行使,是指中央除保留部分权力外,还将大部分管治权授权给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形成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第二,高度自治是一种有明确界限的地方自治。邓小平就曾经明确指出,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澳门特别行政区是高度自治的行使主体,其本身就不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其权力不是无限的。澳门基本法第2条就明确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享有高度自治,而且在第20条就明确中央还可以享有特别行政区以其他权力。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存在着联邦制下的“剩余权力”问题。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仅只能限于特别行政区内部的本地事务进行行政管理;澳门立法会不能对国防、外交和其他不属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立法,法院不能管辖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而只能审判特别行政区内部的案件。
第三,高度自治必须依法行使。这就是基本法所明确指出的必须“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依照本法的规定”,是指依照基本法的规定,这里包括以下几个内涵:(1)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范围不是无限的,而必须以基本法的规定为限;(2)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行使不是任意的,而必须以基本法规定的方式予以行使。[23](3)高度自治是中央授权形成的,中央对授出的高度自治权有进行监督的权力。[24]
三、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运作模式
(一) 两个权力运作的政治前提
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都是建立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前提上。“一国两制”是我国为解决祖国内地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以及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中国主权的问题而提出的基本国策。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内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整个国家的主体,同时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
为了落实“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才有了特别行政区制度,才有了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制度是一体的。正是基于“一国两制”的基础上,中央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在澳门行使全面管治权。中央除直接行使部分权力外,还把大部分直接管治的权力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治理体系的整体。两个权力的运作都是建立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前提上。
澳门基本法序言指出,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澳门的繁荣稳定,是我国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的出发点。不仅要保持澳门特别行政区长期繁荣稳定,而且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是“一国两制”根本宗旨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邓小平在讲到“港人治港”时,指出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25]中央在行使全面管治权,和特区在行使高度自治权时,都必须围绕着“一国两制”这个共同的政治前提以及这个根本宗旨而进行。
(二) 两个权力运作的宪制基础
两个权力运作的法制基础都是建立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的宪制基础上。中央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行使全面管治权,首先是依据中国宪法。中国宪法规定规定了我国的国体和政体,规定了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规定了我国在澳门地区享有不可置疑和不可动摇、不可分割的主权,规定了中央国家机构的一系列权力。根据这些宪法规定及其精神,澳门基本法进一步规定了中央国家机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权力,如修改基本法、解释基本法、任命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立法会法律使其无效等。全面管治权并不指中央在特别行政区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而是要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职权和法定程式展开。
澳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全国人大在澳门基本法里授予给予。而澳门基本法本身是根据中国宪法而制定的。中国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在根本上是中国宪法赋予的。因此,无论是中央的全面管治权,还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其运作的法律基础都是建立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的宪制基础上的。
宪法是我国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根本法律依据。澳门基本法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具体法律保障。澳门基本法的理解和解释,不能离开澳门基本法的立法根据中国宪法。应当从中国宪法所体现的的宪政理念、原则和精神来贯彻基本法和落实基本法。在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运作过程中,不仅要树立基本法意识,而且还要树立宪法意识。应当在宪法确立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正确处理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三) 两个权力运作的相互衔接
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是相互衔接在一起运作。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和有机结合的。
第一,中央有些直接行使的权力,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制度。如澳门基本法第47条规定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就是说,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先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在此基础上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在正常情况下缺乏其中一个环节,行政长官无法产生。
第二,在中央授予特别行政区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方面,基本法明确规定了中央的有关监督权力。如澳门基本法第17条第1款规定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第2款和第3款同时规定立法会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澳门基本法第158条明确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授权特别行政区法院有权对基本法进行解释,然而,法院若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等等。
第三,在有些情况下,中央权力和特区高度自治权力不仅是结合的,而且是交错进行的。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两部基本法附件一第7条和附件二第3条的解释里[26],确立了“政改五步曲”的修改程式,即推动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必须由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第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是否进行修改(第二步),立法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政府提出的修改方案(第三步),行政长官同意(第四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第五步),在这五个修改步骤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和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政府和立法会的权力交错行使,互相推动整个修改程式的前行,这充分说明了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交错结合在一起行使的。
四、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途径
(一)全面管治权引领高度自治权的有效行使
1 中央领导参加特别行政区重大活动和视察特别行政区
中央领导参加特别行政区重大活动和视察特别行政区,既是特别行政区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央在特别行政区显示其主权地位和全面管治权的集中体现。如199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专程到澳门参加澳门回归祖国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庆典,在庆典上发表重要讲话,同时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就职宣誓进行监誓。2004年、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两度来到澳门,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五周年和十周年庆典,监誓新一任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宣誓。201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专程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十五周年的庆典,监誓新一任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宣誓。与此同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吴邦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德江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分别在澳门发展的重要时刻和遇到如非典疫情这种重要困难的时候,都来过澳门视察。
中央领导参加特别行政区重大活动和视察特别行政区,通常发表重要讲话,带来中央的支持和关怀,提出特别行政区的发展方向,帮助特别行政区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是全面管治权引领高度自治权有效行使的重要方式。
2 听取行政长官述职并发出指示和要求
澳门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必须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这种负责是实质性的。正是基于这种实质性负责的理解,澳门回归以来,形成了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述职的制度。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每年向中央作一次述职,报告在特别行政区贯彻落实基本法的情况、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情况,聆听中央领导对特别行政区工作的指示和要求,以体现行政长官对中央负责。
澳门回归后就纳入了我国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行政长官是在澳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央听取行政长官述职并对其发出指示和要求,是确保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引领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效行使的重要方式。行政长官的述职,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向中央、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的范畴,因而不能简单采用行政长官与中央领导面对面互相平等交流工作心得的形式,应当体现出特别行政区在我国单一制国家下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
3 维护“一国两制”在特别行政区的正确发展方向
“一国两制”是我国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后,在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并保持港澳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维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而采取的一项基本方针政策。“一国两制”二十年的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的制定和实施都始终存在着一个主导权问题。单靠香港、澳门自身的力量,单靠“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不足以驾驭全域、把握“一国两制”的发展航向。中央承担着实施“一国两制”的决定者、主导者和第一责任人的角色。[27]
中央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治理结构中既是主权的代表者、权力的授出者、自治的监督者,责无旁贷地肩负着掌控“一国两制”正确方向的历史使命,把握当下,引领未来。中央按照宪法和基本法代表国家对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全面管治权授权形成的,是在全面管治权下运作的。中央通过解释基本法等活动及时解决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提出澳门特别行政区战略性的发展方向,推动澳门提升对外交往空间,以及与内地的合作和交流,维护“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正确发展方向。
(二)全面管治权支持高度自治权的依法行使
1 制定支持特别行政区发展的重大措施
澳门特别行政区与祖国内地的经济关系,基本法中没有特别明确的专门规定,但澳门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中央人民政府理所当然地重视和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民生改善,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回归以来,祖国内地确保对澳门所需的淡水、电力、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专门建设大腾峡水库,从根本上解决澳门吃水受咸潮影响的问题,以及支持澳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非典疫情等风险和挑战。
应特别行政区的要求,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并从国家第十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开始,将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纳入其中,使澳门在国家发展中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中央政府还先后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批准广东省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粤澳合作框架协定》,为拓宽了澳门与内地合作领域,促进澳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2017年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这些都是中央制定支援澳门特区发展的重大措施。
2 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行政长官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整个政治体制里处于核心地位,行政长官既是特别行政区的地区首长,又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行政长官既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也对澳门特别行政区负责。行政长官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主要官员由行政长官提名,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并由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免除其职务。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中,由行政长官和政府所代表和行使的行政管理权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28]
在港澳复杂的社会局面下,行政长官作为在特别行政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的管治权威,容易受到一些极端的反对势力的挑战和冲击。行政长官负责执行基本法,肩负着“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正确实施的宪制责任。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既是中央在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主要的“抓手”和“着力点”,也有助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本身应有功能,有效解决澳门特别行政区内部的住房、民生、福利、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实行长治久安。
3指导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其他地区开展各种交流和合作
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关系,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内地、澳门特别行政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关系。澳门回归以来,已经与我国内地签订多项有关司法协助、经贸合作、教育、智慧财产权合作、避免双重征税、供气供电、海域保护等多个方面的安排、协议、谅解备忘录、联合公告等。澳门特别行政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签有司法协助和出入境方面的协议。促进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内地、香港地区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是中央人民政府在“一国两制”体系里的宪制地位决定的。
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关系,既不属于外交事务,也不属于特别行政区本地事务,而是属于外交、国防之外的其他不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是两岸关系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必须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授权或指导下开展交流和合作。
4 授权或协助特别行政区开展对外交往与合作
澳门特别行政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下有一定的对外交易处理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自主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特别行政区的对外事务权,并非其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形成的。从本质上看,对外事务是国家外交事务的延伸。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或协助特别行政区开展对外交往与合作,是中央全面管治权支援特区高度自治权依法行使的重要方式。
5 协助特别行政区救助当地自然灾害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防务,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驻有军队。澳门驻军的职责,澳门的职责主要在于: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安全、担负防卫勤务、管理军事设施、承办有关的涉外军事事宜。但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澳门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2017年8月23日,“天鸽”风灾造成澳门历史上少有的人命伤亡及严重破坏。行政长官根据澳门基本法和澳门驻军法,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澳门驻军协助澳门救助灾害,并及时得到批准。2017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派出约千名官兵,协助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救助台风“天鸽”带来的重大灾害。澳门驻军经过连续三天的奋斗,累计清理面积107.6万平方米,街道总长约12.05万米,截锯拉运树木约680棵,运送垃圾约700车,在8月28日完成任务返回内地,对澳门加快善后工作起到了积极及突出的贡献。这次驻澳部队支援澳门特别行政区救灾,体现了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关怀,体现了驻澳部队是维护澳门繁荣安定的坚强后盾。
(三)全面管治权监督高度自治权的正确行使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立法会法律使其失效
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澳门立法会可以制定除国防、外交和其他不属于自治范围内事务的法律。澳门立法会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其所属的澳门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后,如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该法律的失效,除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无溯及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发回立法会法律,使其立即失效,这是由于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本身是中央授权所决定。这是中央全面管治权监督特区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的重要机制。
2 建立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的负责机制
行政长官必须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这是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决定。澳门基本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基本内涵就是要求行政长官效忠国家,向中央人民政府述职并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执行,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安排与命令。在执行公职以及与公职相关的行为中,要忠于职守、尽心履职,维护宪法与基本法的权威,维护国家在特区的利益。
行政长官既是中央在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主要抓手和着力点,也是中央监督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
3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
澳门基本法第143条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进行作出解释。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澳门基本法前,征询其所属的澳门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这就说明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必须受制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解释基本法,维护澳门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尤其是正确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构成有力监督。
五、小结:进一步促进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
全面管治权是对单一制国家宪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中央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是在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形成的。我国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自身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并监督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探索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巩固。在“一国两制”今后的实践中,应当进一步促进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
第一,促进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应当进一步彰显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作用和功能。宪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我国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根本法律依据。港澳过去二十年的“一国两制”实践,在治理体系方面,如果说有所不足,就是在于对宪法在港澳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认识得不够、强调得不够。应该充分认识宪法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只有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才能从整个宪制的高度促进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
第二,促进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应当进一步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的相关制度和机制。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是指进一步落实好中央管治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机制,使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切实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运行,将中央的具体权力与特区的具体机制进一步衔接,从而落实好澳门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内部的有效实施。尤其在诸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立法会法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以及行政长官述职、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指令等方面,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与之对应的制度机制,细化有关规定。
第三,促进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应当进一步提升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将特别行政区治理体系理解为一个整体,既包含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也=包括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所谓高度自治的名义来对抗中央在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应当建立在进一步提升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完善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制建设,培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治理队伍,提升公共行政能力,从而有力促进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
注释︰
[1] 可参考孙关龙、孙华:《关于中国古代两种地方政制的初步研究》,载《一国两制研究》第9期,2001年7月。
[2] 王禹:《论恢复行使主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4-177页。
[3] 中国宪法(1982年)第62条第(二)项和第67条第(一)项。
[4] 博丹的《共和六书》出版于1576年,用法文发表,十年之后,即1586年,博丹自己将其译成拉丁文发表。在1576年的法文版里,博丹指出“主权是共同体所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力”,在其拉丁文版里,博丹还补充说,”主权是凌驾于公民和臣民之上的最高的和绝对的权力。”见【法】让‧博丹:《主权论》,【美】朱利安H佛兰克林(编),李卫海、钱俊文(译),邱晓磊(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页及其注2。博丹的《共和六书》有的中译本也译为《国家论》或《共和六论》、《论共和国》。
[5] 《牛津法律大词典》单一制条。
[6] 张元元:《澳门法治化治理中的角色分析》,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第98页。
[7] 邹平学、潘亚鹏:《港澳特区终审权的宪法学思考》,见《成功的十年: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纪念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19日,北京大学。
[8] 王禹:《论恢复行使主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7页。
[9] 马岭:《特别行政区长官“述职”之探讨》,载《比较法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3-144页。
[10] 还可参见王振民:《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18-119页,及李林:《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及其实践》,载《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
[11] 许崇德:《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5页。
[12] 见胡肖华:《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践与背离》。
[13] 廉希圣教授认为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具有“权”、“人”、“财”三个要素:(1)权:高度自治权;(2)人:澳人治澳;(3)财:财政自主,见其《中央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系的特点和价值目标》,载萧蔚云、杨允中、饶戈平(主编):《依法治澳与稳定发展-澳门基本法实施两周年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出版,2002年。
[14] 焦宏昌主编:《港澳基本法教程》,第86-87页。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1988年4月28日)第15条。
[16] 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第109页。
[17] 此处可以参考香港基本法的英文本第2条译法,“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independent judicial power, including that of final adjudication”。
[18] 还可参考杨静辉、李祥琴:《港澳基本法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3-175页。
[19] 澳门基本法第11、135条等。
[20] 澳门基本法第136条。
[21] 澳门基本法第142条。
[22] 此种情况还涉及到该国是否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澳门基本法对此作了区分:(1)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澳门设立的领事机构和其他官方机构,可予保留。(2)尚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在澳门设立的领事机构和其他官方机构,可根据情况予以保留或改为半官方机构。(3)尚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国家,只能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民间机构。
[23] 还可参见李林:《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高度自治及其实践》,载《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及《香港基本法读本》,法律出版社,2009年。
[24]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
[25] 见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第61页。
[26]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条及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2004年4月6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2011年12月31日)。
[27] 饶戈平:《准确实施一国两制 全面落实治港权力》,香港商报,2017年5月30日。
[28]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2014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