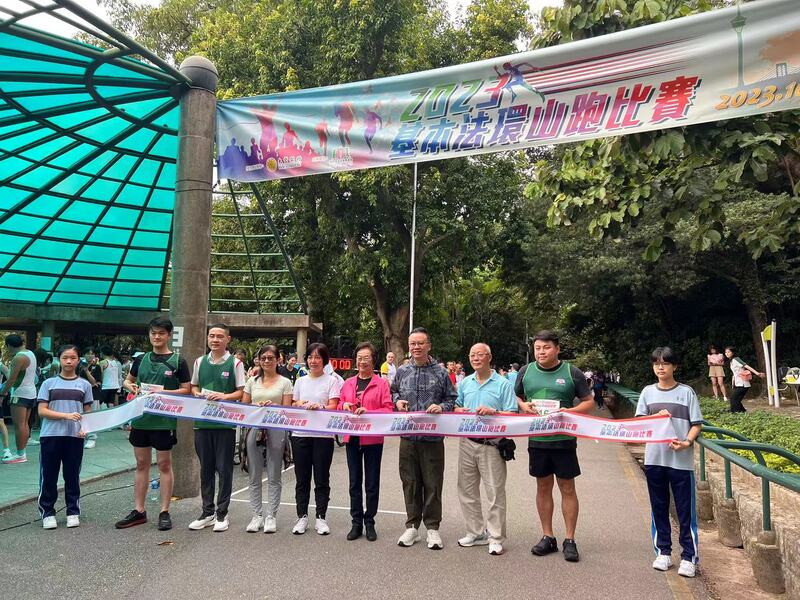在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中央明确提出了“全面管治权”的概念,认为中央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1]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2]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也再次强调了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对于“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意义,认为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中央拥有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的提法和论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引发了社会对中央的这一提法和论断是否具备法理基础以及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是否会侵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等争议或担忧。为此,本文拟对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概念、作用及其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等几个主要问题作出分析,以期对“一国两制”下中央与特区关系的处理以及“一国两制”在特别行政区的全面准确理解和有效贯彻落实有所帮助。
一、什么是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
对“全面管治权”的理解离不开对“主权”、“治权”、“管治权”等概念的理解。实际上,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是以中央对特区的“主权”、“治权”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概念。
(一)主权
《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认为主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行管治的最高的(supreme)、绝对的(absolute)、不可加以限制的(uncontrollable)权力”。[3]《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主权是现代国家最根本的属性,“指拥有充分的权力维护对外独立,对内忠诚和秩序以及在其领土内规定、适用和解释法律制度的最高权和独立权”。[4]《宪法学词典》认为,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处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而不受他国干预或限制的最高权力。在对外关系上,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在对内方面,国家享有最高权力,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前者为独立权,后者为统治权,两者密切联系,构成完整的独立概念。”[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主权是国家所固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不可或缺的属性。主权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内容。在对内层面上,主权是指由作为主权者的国家所享有的对其领土内的一切区域和一切事务的最高统治权,国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统治。而在对外层面上,主权则是指作为主权者的国家所享有的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行使对其领土内一切区域和事务的统治权,而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干涉的权力,即有权排除其他国家对于本国领土内一切区域和一切事务行使统治权。
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独立、统一的国家主权,整个国家的主权统一由中央政府(广义)行使。港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始终拥有对港澳的主权,英国和葡国长期占领并管治港澳的事实并不能改变港澳属于中国领土的性质,也不能使中国政府丧失对港澳的主权。因此,中央政府(广义)代表我国拥有对包括港澳在内的我国领土范围内所有区域的主权。具体而言,在对内层面上,中央政府有权对我国领土内的一切区域和一切事务行使最高的统治权,统治权专属于中央政府行使,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任何地方行政区域均不能行使这一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在对外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任何其他国家均不能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际法上的主体,特别行政区由于不享有国家主权,因此不能以国家或独立政治实体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不能参与要求以国家主体身份参与的国际事务。其能够以“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国际公约,也是获得中央授权的结果。
(二)治权与管治权
“治权”是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过程中由英国政府提出来的概念。在中英谈判的第一阶段,英国政府坚持认为中国政府(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在国际法上是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后政府”应当承认“前政府”所签订的条约,继承“前政府”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因此香港的主权应属于英国。在中国政府明确表明主权问题不容讨论之后,英国政府并又提出了“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主张1997年以后,英国政府将香港名义上的主权归还中国政府,但仍由英国政府继续管治香港,即香港象征意义上的主权由中国政府拥有,但香港的治权则由英国政府行使。对此,中国政府坚持认为三个不平等条约是无效的,认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香港始终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的主权始终属于中国。同时认为将主权与治权分割的做法也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指包括恢复行政管理权在内的完整主权,而不是一个架空的名义上的主权”。[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英谈判过程中提出的“治权”的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国家对特定区域进行管辖和治理的权力,也就是国家对特定区域的实际管治权。[7]从这个意义上说,治权与管治权是类似的概念。虽然如果单纯从语义上看,治权强调的是治理的权力,而管治权则强调管辖权和治理权的结合;但从实质上说,要行使治理权必然首先要求拥有管辖权,拥有管辖权是行使治理权的前提,因此治权实际上也是管辖权和治理权的统一。
从理论上说,主权与治权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主权意味着作为主权者的国家有权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一切区域和一切事务行使最高的统治权,同时排除其他国家对于本国领土内一切区域和一切事务行使统治权。那么国家如何行使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一切区域和事务的统治权?就是要通过行使对这些区域和事务的治权来实现对该国领土范围内一切区域和事务的管辖和治理。换言之,要行使对一国领土范围内一切区域和一切事务的统治权,其前提是必须拥有该国的主权;只有拥有一国主权的主体才能拥有对该国领土范围内一切区域和事务的最高统治权,因而也才能合法行使对该国领土内一切区域和事务的治权(管治权)。而反过来说,作为主权者的国家要想真正实现对本国的主权,实现对本国领土内一切区域和事务的最高统治权,使其对本国所享有的主权由法律上的概念转化为对本国的实际管辖和治理,就必须通过行使对本国领土内一切区域和事务的治权(管治权)来实现。因此,主权是治权产生的依据和合法性基础,不享有主权,就不能合法行使治权。[8] 治权是实现主权的途径和行使主权的方式,主权的实现必须依靠治权的行使,不行使治权,主权就只能停留在法律层面或字面意义上。
在“一国两制”背景下,港澳回归的实质是主权行使的回归,即中国政府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而主权行使的回归实质上是治权的回归,中国政府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就是要彻底结束英国和葡国政府对港澳行使治权,而改由中国政府行使对港澳的治权。中国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绝不仅仅是名义上或形式上的举措,“绝不是图个名声、摆个样子,而是意味着实实在在地恢复行使国家对港澳地区的‘最高的、绝对的、不可加以限制的’主权权力,意味着全面地切切实实地实施国家对港澳的管治。”[9]如果中国政府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仅仅意味着中国政府享有对港澳名义上的主权,而不能行使对港澳实质意义上的治权,那么中国政府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政府之反对英国政府提出的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原因就在于“这个主张的实质是抽象肯定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具体否定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10]因此在回归以后,在中国政府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的情况下,港澳的主权和治权都属于中国,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对港澳的主权及相应的治权,实际管治港澳。任何其他的国家或实体都不享有对港澳的主权,因而也不能行使对港澳的治权。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中央政府(广义)对港澳的治权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中央政府(广义)有权决定通过将宪法适用于港澳及制定相关宪制性法律(即基本法)的方式将港澳纳入中国的宪政体制和宪政秩序中,有权决定在港澳设立地方行政区域并决定港澳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有权规定在港澳实行的制度,等等。这些权力都是实质性的权力,是中国政府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政府作为主权者对其主权下的港澳地区所必然应当享有的权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治权和管治权实际上是大致相当的概念,指的是基于主权而产生的,由作为主权者的国家所享有的对其领土内的一切区域和事务进行管辖和治理的权力,是实现国家主权的途径和行使国家主权的方式。
(三)全面管治权
如前所述,管治权与治权是大致相当的概念,在港澳回归以后,中央政府行使对港澳的管治权(治权)是中国政府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的应有之义,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必然就能够行使对港澳的管治权(治权),能够实际管治港澳。而全面管治权在性质上也属于管治权(治权)的范畴,在管治权前面加上“全面”二字并不意味着全面管治权与管治权或治权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二者在本质上都属于国家对其领土内一切区域和事务进行管辖和治理的权力。
在此情况下,之所以可以在“管治权”前面加上“全面”二字,明确中央对特区享有“全面”管治权,其法理依据主要在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央对特区的管治权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全面管治权”的法理基础。中国政府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必然意味着中央政府能够行使对港澳的管治权,而由于我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人民将国家权力完全托付给中央,“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所有权力都是属于中央的”,[11]由中央根据国家管理的需要决定将部分权力“转授予”地方;地方本身没有权力,地方享有的所有权力都来源于中央的授权。因此,从理论上说,在单一制下,作为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的主体,中央政府对本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和所有事务都具有管辖和治理的权力,概括来说就是中央享有对本国领土范围内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全面管治权。概而言之,所谓“全面管治权”可以表述为基于国家主权而产生的,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对我国领土内所有地方行政区域以及所有事务进行管辖和治理的权力。而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我国单一制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央自然也享有对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
二、为什么要强调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
强调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强调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有利于明确中央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的具体内涵,保障中央依法行使对特区的管治权。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是基于中央对特区的主权所产生的、由我国宪法和规定所规定和保障的实实在在的权力,是我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对于这一权力,中央应当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依法行使,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否定、对抗或非法限制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张德江委员长在2017年5月27日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是恢复行使包括管治权在内的完整主权,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在此基础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了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管治权的方式,即规定了一部分权力由中央政权机构直接行使,一部分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行使,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高度自治权。维护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来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
在“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对中央管治权的曲解或误解。比如,有人刻意忽视或淡化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规定所享有的对特区的管治权力,认为中央对特区的管治权力仅限于国防和外交方面的权力,提出诸如“基本法定下的香港特区的权力,是除了国防与外交之外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12]“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的关系,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除了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区在其他范畴均享有高度的自治权”[13]等错误观点。这些观点实质上就是对中央管治权的否定、抗拒或非法限制。而强调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明确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国家主权所产生、受到宪法和基本法保障的权力,是不容否定、对抗或非法限制的权力,正是对这些错误观点或行为的纠正和回击,[14]有利于促进人们全面准确理解基本法,保障中央依法行使权力,维护基本法的权威。
其次,强调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有利于填补“主权”与“高度自治权”之间存在的理论断层,进一步从理论上明晰中央对特区的主权是如何通过授权而形成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的。根据“一国”的原则,中央享有对特区的主权,而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那么中央对特区的主权是如何通过授权而形成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的?由于主权不可分割也不可让予,中央不可能将自己享有的对特区的主权完全或部分授予特区,特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也不可能是主权或主权性的权力,因此要解释中央对特区的主权如何通过授权而形成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就需要在“主权”和“高度自治权”之间增加一环,那就是“全面管治权”。因为中央享有对特区的主权,中央就享有对特区的管治权,而又因为我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中央对特区的这种管治权又可以被称为“全面管治权”。在行使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时,中央既可以将一部分权力保留由自身行使,这就成为了中央对特区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可以将一部分权力授予特区行使,这就成为了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在此过程中,中央授予特区的并非主权或主权性权力,而是对特区的部分管治权。[15]经中央授权,特区就有权依法行使中央授予的部分管治权,这就没有违反主权不可让予也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也更能清楚地表明特区高度自治权不属于固有权力的根本属性。换言之,中央对特区的主权产生了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而中央对特区全面管治权的行使又产生了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基于这一逻辑,“全面管治权”就在“主权”与“高度自治权”之间构建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16]填补了“主权”与“高度自治权”之间存在的理论断层。
最后,强调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有利于明确中央与特区之间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明确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从而有利于澄清许多对“一国两制”的不全面或不准确的理解。
既然从理论上说,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对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都享有“全面”的管治权,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中央,地方行政区域本身并没有固有的权力,其所享有的权力都来源于中央的授权。那么特别行政区作为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域,自然就不享有原始的、固有的权力,更不享有自决的权力,其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无论范围有多广、程度有多高,都不能改变其来源于中央授权的根本属性。中央的授权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来源与合法性基础。
既然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那么中央授予特区多少权力,特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中央没有授予特区的权力,自然就保留由中央享有,而不属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范畴,因此特区就不存在所谓“剩余权力”[17]的问题,凡是中央没有通过基本法或者其他的形式授予特区的权力,都属于中央的权力,而不属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中央对特区的权力自然就不仅限于国防和外交方面的权力,而应当是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以及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在内的全面管治权。
既然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那么作为授权者,同时也是“兜底责任”的最终承担者[18]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最终“所有权”人[19],中央自然有权对授予特区的权力进行监督。从另一个角度说,作为被授权者,特区享有并行使中央授予的权力是有条件的,其在行使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时不能破坏“一国”的原则,还必须同时承担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为了保证特区行使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的行为不违背“一国”的原则,保证特区切实履行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中央自然有权对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基本法也规定了一系列中央对特区的高度自治权进行监督的权力,包括对特区的财政预算、决算进行备案监督的权力;接受行政长官述职和报告的权力;对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备案审查并决定发回的权力;对属于“国家行为”的案件进行司法管辖并对“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作出认定的权力;等等。实际上,作为授权者、“兜底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以及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最终“所有权”人,除了对特区高度自治权进行监督的权力之外,中央还享有其他对特区高度自治权进行制约或限制的权力,比如中央有权依法追加对特区的授权或对已授予特区的权力进行调整,有权决定授权的期限和条件,有权在授权期限届满后,决定取消或延续对特区的授权,等等。这些权力,与中央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一样,都体现了高度自治不等于“完全自治”,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必须受到中央的限制。
三、强调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与保障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
不少人士之所以对中央享有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的提法表示出一些质疑或顾虑,主要是担心其会否侵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实际上,这样的顾虑但并没有必要,强调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与保障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之间并不矛盾。
首先,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并不是一对互相矛盾、对立的概念,相反,二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一国两制”实践和特别行政区治理过程中。
中央全面管治权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来源与基础,特区高度自治权是中央全面管治权的组成部分。中央之所以能够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其依据就在于中央享有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本身就是中央行使对特区全面管治权的方式之一;而特区之所以能够享有并行使高度自治权,是中央行使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向特区授权的结果,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是中央行使对特区全面管治权的体现。中央的全面管治权是基于我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以及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而形成的对特区所有事务进行管治的权力的总和,而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则是基于中央的授权而形成的对中央授权所确定的特区特定事务进行管治的权力的总和。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包含了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并从属于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并受到全面管治权的限制(包括但不限于监督)。二者之间存在包含与从属的关系,有层级之分,但并不是一对互相矛盾、对立的概念。
其次,强调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并不是要否定、排斥或取代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也不是要非法限制、改变或破坏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只要中央依法规范行使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就不会构成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侵犯。
中央享有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与中央如何行使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中央享有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是由我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以及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的,它从权力性质和来源上表明了中央对特区的管治权是原始的、全面的权力,而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则是派生性、有限的权力。而中央如何行使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则属于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的方式问题,中央行使对特区全面管治权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由中央决定。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并没有选择特区的所有事务都由中央直接进行管治的方式来行使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而选择了中央直接管理与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并由中央依法对特区的高度自治进行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来行使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即中央一方面依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而直接行使对特区的部分管治权,对特区自治范围以外的事务进行直接管理;另一方面也依法授予特区一定的权力,即高度自治权,由特区在中央授权的条件和范围内依法行使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管理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对于授予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还享有监督的权力。因此,全面管治权中的“全面”指的是在我国政府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的事实以及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从理论和权力来源上说对于特区的所有事务中央都有权进行管辖和治理,中央对特区的管治权是原始的、全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要“全面接管”特区,要收回已授予特区的高度自治权而对特区的所有事务都进行直接管理。中央拥有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的提法只是对“一国两制”方针基本内涵和应有之义的重申,是对“一国两制”下中央依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所享有的对特区的管治权力的强调,而不是对“一国两制”方针基本内涵和精神的重构、改变或破坏,不是要以中央全面管治权去否定、排斥或取代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特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受到宪法和基本法保障的,虽然中央拥有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中央也不能随心所欲、非法任意地行使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不能侵犯特区依法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必须严格遵守法治原则,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及其精神依法规范地行使全面管治权,既依法行使对特区的直接管治权,又依法授权特区实行高度自治,对于授予特区的高度自治权还依法进行监督。只要中央是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宪法、基本法的框架内依法规范行使权力,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就不会构成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侵犯。
註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3] Black’s Law Dictionary, West Publishing Co., 1979, p.1252.
[4] 《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50页。
[5] 赵喜臣主编:《宪法学词典》,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4页。
[6] 鲁平口述、钱亦蕉整理:《鲁平口述香港回归》,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7] 只不过英国政府认为主权与治权可以分割,香港的主权由中国政府享有,而香港的治权则由英国政府行使;而中国政府则认为主权与治权是不可分割的,享有主权就必然意味着能够行使治权,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必然意味着中国政府能够行使对香港的治权,能够实际管辖和治理香港。
[8] 在特殊情况下,治权也可能产生主权,例如根据国际法上“时效取得”领土的方式,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抗议或反对的情况下,连续实际占领和控制管理某一土地达到一定的期限以上,即可获得对该土地的主权。但这种“时效取得”的方式必须符合严格的法定条件,比如该国对某一土地的占领和管治是在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抗议或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对该土地的占领和管治必须达到一定的期限。而英、葡两国是以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形式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强行占领了港澳。在港、澳被英、葡两国占领并管治之后,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港澳的主权,英、葡两国显然不能依据“时效取得”的方式取得港、澳的主权。
[9] 饶戈平:《一国两制与国家对港澳地区的管治权》,载于《中国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第12页。
[10] 骆伟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新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11] 【英】戴维•M•沃克著,李双元等译:《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3页。
[12] 李怡:《香港高度自治权并非来自中央》,载于《苹果日报》,2007年6月9日。
[13] 郭荣铿:《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香港立法会立法?》,载于《明报》,2012年12月10日。
[14] 饶戈平:《如何正确理解“中央全面管治权”(下)》,载于《大公报》,2018年1月18日。
[15] 当然,授权仅仅意味着权力“行使”的转移,而不意味着权力“所有”的转移。中央将部分权力授予特区,特区可以行使这部分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就放弃或丧失了这部分权力,权力本身还属于中央,中央仍保留相关权力的最终“所有权”。相关论述可参见王禹:《“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授权理论研究》,载于《港澳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2013年春季号,总第29期,第109-111页。
[16] 王禹:《论全面管治权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指导意义》,载于杨允中、饶戈平主编:《开拓“一国两制”实践新征程——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22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2015年版,第212页。
[17] 所谓“剩余权力”问题是指在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对于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属于联邦政府或成员单位政府享有的权力,或者对于联邦政府和成员单位政府享有的权力规定不清楚的,应如何处理,即推定由哪一方享有的问题。
[18] 程洁:《中央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以基本法规定的授权关系为框架》,载于《法学》2007年第8期,第65页。
[19] 授权仅仅意味着权力“行使”的转移,而不意味着权力“所有”的转移。中央将部分权力授予特区行使而形成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但中央仍保留对已授出权力的最终“所有权”。相关论述可参见王禹:《“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授权理论研究》,载于《港澳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2013年春季号,总第29期,第109-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