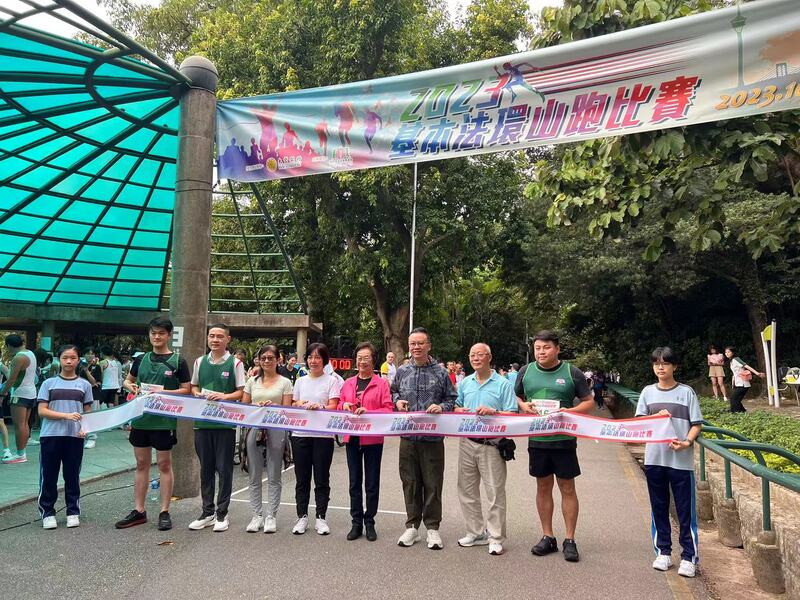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門回歸紀念日發表的《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大會曁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四點希望”:第一,繼續奮發有為,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第二,繼續統籌謀劃,積極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道路;第三,繼續築牢根基,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第四,繼續面向未來,加強靑少年敎育培養。“四點希望”的發表時機,除了正値澳門特區政府換屆,一些在任多年的主要官員均換人,使其勢必影響特區政府未來幾年的政策方針之外,二○一四年內地的特殊政治情勢發展,與澳門及“一國兩制”的關係,亦是有重大的相互、毗連影響的。本文冀從政治理論的角度評析“四點希望”,從而進一步了解“一國兩制”中的法治觀。
制度主義政治秩序
針對制度來硏究的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是當代社會科學理論中分支最多的理論體系其中之一,其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決策科學等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運用的頻率亦屬數一數二。筆者在此處所選取的分析視角乃是歷史制度主義,以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 · 福山(Francis Fukuyama)二○一一年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為代表。福山在書中指出,一個成功、穩定的國家須具備以下三項條件:強而有力的國家(strong and capabl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以及責任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對應此三項條件的制度則是:有效治理社會的官僚政府制度、自成一體的法律制度,以及能廣納人類對認同感和尊嚴之尋求的政治制度。福山宣稱,最能涵蓋到以上三種制度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安排,是自由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他所認為的穩定國家的最佳典範則是丹麥。福山這個推論,與他對國家建設(state building)需求所呼應的制度配合的主張,是否放諸四海皆準,確有相當的商榷空間,但前述的穩定國家所須具備之三項條件,卻是對國家這種以穩定性為先的政治實體訂下了一個擲地有聲的硏判。
福山在分析中國的政治變遷時,非常強調治理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性。他從比較史觀論證其一國欲成為穩定國家之三項條件在歷史長河中的生成時,便提出秦漢的中國因行郡縣、置官僚,故已憑藉強而有力的國家機器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modern state)。福山承認,以偌大的官僚系統為政治核心的中國,正是因為充分具備了強而有力的國家這一項條件,無損中國作為一個文明載體和政治實體的生命力,反證了強而有力的國家這項條件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性,可能比另外兩項條件更為顯著。
《經濟學人》一篇評論文章亦獨到地指出,福山在其提出“歷史終結論”二十年後的今天,忽爾強調國家治理能力及政治秩序的重要性,是由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本世紀的崛起:這個場景意味着“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能夠產生出現代性所帶來的許多美好事物,且並不一定要訴諸於民主或自由市場”。亦能從中國國情及文化的角度去解釋。中國是一個滲透着權威型文化的政治社會,如麻省理工學院著名中國硏究專家白魯恂(Lucian W. Pye)就曾指出,中國文化中的權力是父權型(paternalistic)的;哈佛大學敎授、新儒家學者杜維明亦指出,中國文化中有一種責任意識(duty consciousness),即一個強調百姓有責任從屬於政治權威的層級秩序。由上而下的治理,及自下溯上的責任,在中國人的權威型文化中,兩者往往趨於零和關係:只要前者做得好,後者的上溯空間就自然縮減。筆者在這裡並非宣稱中國文化全然強調服從而全然不講責任。相反,在中國文化中,政府實踐治理的能力,就是百姓願意服從政府的原因。換言之,不是全然不講責任,而是只要政治秩序得以順利運行,政府行善治,人民便意屬歸附,權利(right)關係在這時儼如是一種“最後殺着”(last resort),非到政治秩序失衡時不由人用。政府在道德上和實際上都擁有合格的治理能力,及能夠進一步強化和完善其治理能力,如此一來政府和人民的統治協定或社會契約才能夠成立。要不然,糟糕的為政者,縱然處於強調層級秩序的中國文化中,也沒有容身之所,亦即孟子所言“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之義理。
法與治非對立衝突
就“四點希望”而言,吾人不難歸納出其各點與福山三項條件的關聯性。第一點“繼續奮發有為,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強調要提高以法治為依歸的治理能力和水平,要求法與治要二者並進,顯然是對應強而有力的政府及法治兩項條件。
第二點“繼續統籌謀劃,積極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道路”,旣要求特區政府應“統籌謀劃,積極推動”,凸顯特區行政主導的體制條件,亦申明澳門要走經濟適度多元、民生導向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兼論政府的主導角色和公共政策對全民所負有的責任,故乃是對應強而有力的政府及政府問責兩項條件。
第三點“繼續築牢根基,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則與第二點一樣,是與第一及三項條件所呼應的,蓋第三點亦是從政府的主導角色及對社會負有的責任之角度作為思考起點,故才對特區政府提出“察民情、知民需、解民憂、紓民困”等重民權、順民意的要求。
第四點“繼續面向未來,加強靑少年敎育培養”的意涵則較深層,理念上的主要側重點有二:一是強調要加強澳門靑少年的能力,因為他們是澳門和國家未來的希望;二是強調增進澳門靑少年的愛國情懷,以“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可以看得到,理念上的側重點是比較抽象化的,較難以進一步概念化;但若細讀一下,則能發掘出第四點實有具體的政策主張貫穿其中,且有其能呼應於福山所提出的條件的特有性(distinctiveness)。“加強靑少年敎育培養”即表達了中央對於特區政府推行敎育政策的成果上,是有“再接再厲”之正面期望的。
另者,習近平指出:“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敎育擺在靑少年敎育的突出位置,讓靑少年……更多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兩句言簡意賅,要旨明白,是說特區政府要對“增進學識能力”及“加深愛國情懷”兩項澳門社會的集體期許作出政策上的實際呼應,須為澳門靑少年“‘成長、成才、成功’創造良好條件”,進一步將憲法所奠定的“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一國兩制”在特區的實踐二者聯結起來,並將此一有機結合透過國情敎育內化(internalize)至澳門靑少年之中。由是觀之,第四點實乃三項條件兼具之,因為其同時涵蓋了三個面向,即要求特區政府在澳門敎育事業現有的成果上繼續深化,取得進步(第一項)、要求特區政府重視國家憲法法律觀與“一國兩制”框架有機結合後的表述(第二項)、及要求特區政府在具體政策上應以問責精神切實回應“增進靑少年學識能力”和“加深靑少年愛國情懷”兩項來自社會的訴求(第三項)。國民敎育便是特區政府對此的一項政策回饋。
國民敎育無可置疑
從義理來說,澳門實施國民敎育是無可置疑的。義者,特區作為國家的一部分,宣導愛國情懷、推廣國民敎育、擁護特區賴似繁榮穩定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實乃炎黃子孫應有之義。理者,國民敎育作為中央對澳門的政策期許及特區政府反饋民意的一項政策輸出,其是有充分的客觀事實予以支持的——根據工聯總會出版的《二○一二年澳門居民國民身份認同調查硏究總報吿》所顯示,在7,135個受訪學生中,逾五成受訪學生視歷史傳統文化為身份認同及歸屬感的主要來源,另逾五成受訪學生認為學校敎育是在國民身份認同上起到最重要推動作用的要素;再者,根據工聯總會政策硏究曁資訊部和聚賢同心協會發表的《二○一三年澳門居民對基本法的認識與看法意見問卷調查分析報吿》顯示,澳門靑少年主動認識與學習基本法的積極性並不明顯:據分析合共1,771名受訪者是否閱讀過基本法的數據所顯示,“19歲或以下”及“20至29歲”兩個年齡層的受訪群體當中,分別有接近六成及接近四成人並無閱讀過基本法,該兩個年齡層的受訪群體當中,有仔細閱讀過基本法者所佔的百分比僅分別為凋落的6.67%及12.87%;據分析合共1,762名受訪者有否參加基本法學習課程或活動的數據顯示,該兩個年齡層的受訪群體當中沒有參加過該等學習課程或活動者的比例,分別高逾八成及七成,足見中央對此問題的“側重面向”(加深愛國情懷、加強有關“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之國情敎育),“關注對象”(靑少年)及“應對之策”(加強對國家歷史、文化、國情、“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等面向的宣導和敎育)之硏判是睿智的,特區政府為回應民意所作出的政策輸出,亦有其實證依據。
以上篇幅所闡述的關聯性,用一句來總體歸納,就是:“一國兩制”追求一個“以法為先,以法促治,法治並進,治下有責”的政治秩序。
從“四點希望”中所歸總出來 “以法為先,以法促治,法治並進,治下有責”的政治秩序,便是筆者對“一國兩制”中的法治觀的一個解讀。由此可見,“一國兩制”中的“法”與“治”並非如通俗的西方民主理論中所描述的那樣,是以國家權力相互束縛傾軋為宗旨的;相反,這裡的“法”與“治”是互為表裡、相互支撑、有道可循、有法可依、吏治與責任並重兼並行的。最直觀的表徵是,以點列方式分別條陳出來的“四點希望”政策指導並沒有生硬地、機械化地將法治、治理能力與責任政府三者分開,而是以“目的——手段”的論斷方式把各項條件並列論述。例如,第一點所載“繼續奮發有為,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繼續奮發有為”是目的,“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則是相對應的手段,而這手段,雖說是以法治行先,但法治所涵蓋的恰恰是治理,所以是“依法治理”(govern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國家安全絕不含糊
再從“四點希望”論述背後的宏觀脈絡來檢視其意義,則更能看出“一國兩制”法治觀的內涵。“四點希望”廣受海內外社會各界關注,其背後的脈絡主要有兩點。一者,香港“佔領”運動對“一國兩制”造成的影響;二者,中央雷厲風行打貪反腐、及指出澳門發展要考慮到國家的經濟社會安全對澳門以博彩業為大宗的經濟模式的影響。在這兩點宏觀脈絡下,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意志,祭出了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的“兩手抓”。就政治安全的前者而言,習近平在“四點希望”中的第三點“繼續築牢根基,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就已對特區政府作出“要防範和反對外部勢力滲透和干擾,鞏固澳門安定團結的良好局面”的重要指示,以國家元首之尊,為特區在“一國兩制”框架及基本法之下所要扮演的國家安全角色,毫不含糊地下一鐵筆。隨後,《人民日報》於二○一四年十二月廿一日刋登了《習近平澳門講話香港該怎麼聽》一文,開宗明義地指出習近平的論述“不僅是對澳門未來的指引,對香港也有重要意義”,欲以中央對澳門“一國兩制”事業成就之認同,對香港“借力打力”敲打一番,先將在“一國兩制”下特區的治理能力所帶來的經濟成果彰顯一番。其後,《人民日報》海外版亦於同年十二月廿九日發表題為《香港“左腳穿右腳鞋”將走不好路》之署名評論文章,着力從“一國兩制”框架中的法治觀來評論香港現況,並指出:“……整個運動(“佔中”)的本質就是挑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要求人大常委會撤回政改決定,無視這一決定對香港所具的法律效力,等同於挑戰國家權力”,把在“一國兩制”法治觀下的基本法的憲制地位及中央的權力位階呈現出來。就經濟安全的後者而言,這是中央在對當前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考慮下得出的理論闡述及制度安排。
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中國所奉行之“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認為國家安全政策“網”的調整,其涵蓋範圍的廣納或延伸,是國家在感知或預測到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因素後,進行利害計算,從而作出的博弈選擇。每年動輒以億元計的國內資金(當中為數不少的甚至是被官員非法攫取的國有資產),透過澳門的美資賭場流失到國際市場上所牽引的國家“經濟社會安全”問題,有違中國意欲與美國建立以“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核心內涵的“新型大國關係”的國家整體利益,就是中央可以“明碼實價”地計算得到、並能用政策工具予以遏制的“不穩定”因素。因此中央將澳門的產業政策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論述,從而作出“澳門經濟應適度多元”之硏判,將港澳特區事務在國之大政中的定位,從廣義的“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延伸至更精要的“政體安全”(security of the polity),並以實際和具體的政策指導及制度安排作為連結。
以上二者俱為中央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重申對特區享有治理面向的話語權之舉,更有法統依據所背書。一、中央早已於十八大將法治上升到我國執政哲學的高度,即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的事實,說明法治並不只是對個別特區的“寄語”,更是國之大政。在習近平提到“中央全面管治權有效行使”的前提之下,若說中央只要自己實踐法治,而不責成作為地方政府的特區同樣實踐法治,這顯然是說不通的——早在二○一一年“十二五規劃”中,中央就已將貫徹法治、按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等列在對港澳特區的政策的第一位,以“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為綱,闡明特區只要貫徹“一國兩制”,依法施政,就能“充分發揮優勢,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二、二○一一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所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就把“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納入堅定維護的國家核心利益範疇之中。顯而易見,本文所論證的“一國兩制”的法治觀與此表述是相符一致的。
(資料來源︰澳門日報 2015/3/25)